瓦格纳老板为何叫普里戈任,而非普里戈津
最近红遍全球的人不是普京,不是泽连斯基,也不是拜登。
而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老板普里戈津。

(瓦格纳的坦克)

(普里戈任,也有人音译为普里戈津)
你一上网,几乎到处都是普里戈津、普里戈津、普里戈津……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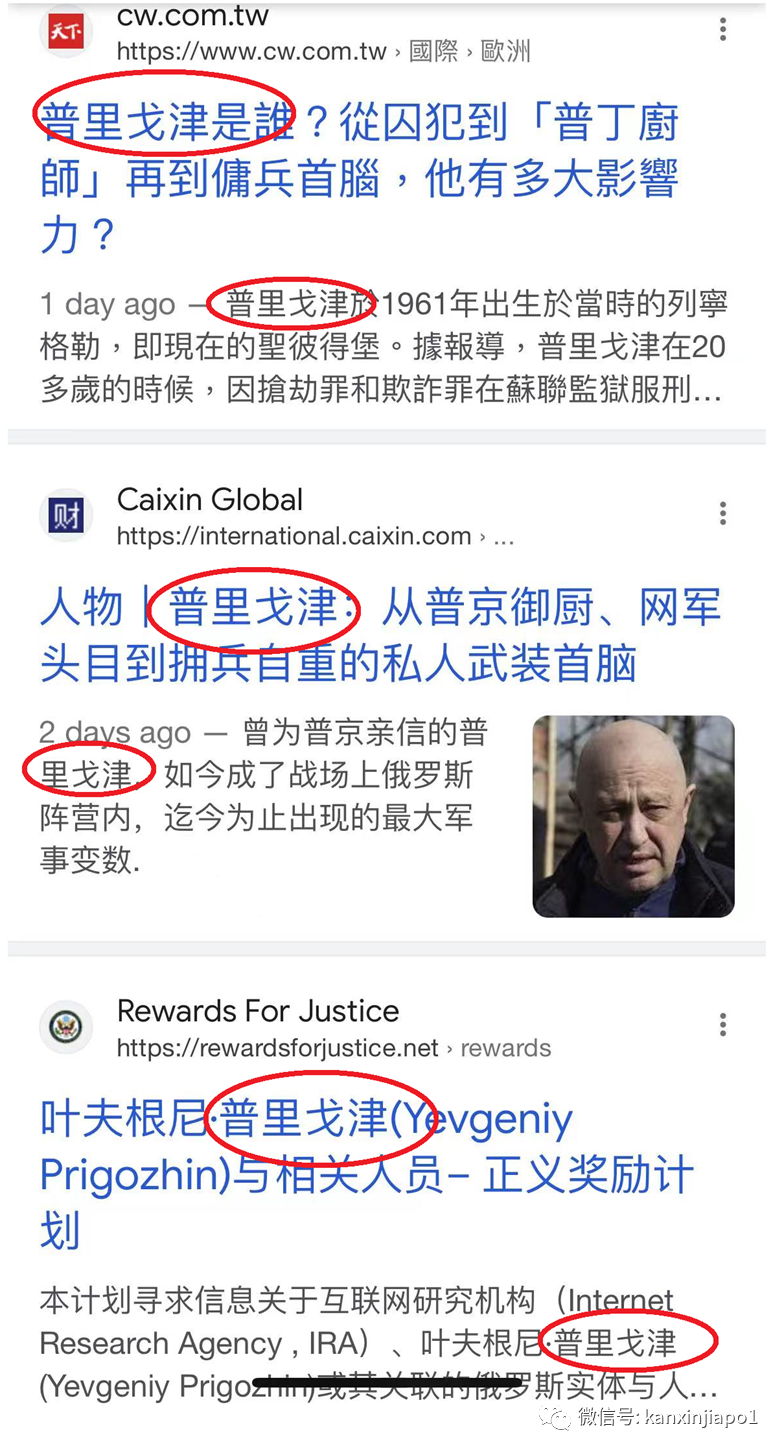
真是“平生不识陈近南,纵称英雄也枉然”。
欸!不对!
在到处一片“普里戈津、普里戈津、普里戈津……”声中,笔者突然发现,还有不少媒体称他为“普里戈任”。

他名字“Prigozhin”,音译为普通话/华语,“普里戈津”没错啊,为什么这些主流大媒体还音译为“普里戈任”,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?
于是,我去查最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俄语姓名译名手册》。

Prigozhin的俄语拼写为Пригожин,罗马化之后写为Prigozhin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俄语姓名译名手册》第一版和第二版中,“zhin”这个音节都被译为“任”,比如苏联克格勃的前身“契卡”创始人Felix Dzerzhinsky的正式译名为“菲利克斯·捷尔任斯基”,俄罗斯政治家Vladimir Kozhin的正式译名为弗拉基米尔·科任。
其他姓Prigozhin的名人包括音乐制作人Iosif Prigozhin(约瑟夫·普里戈任)、苏联作曲家、人民演员Lyutsian Prigozhin(柳齐安·普里戈任)、苏联/乌克兰科学家Efim Prigozhin(叶菲姆·普里戈任)。
因此,瓦格纳集团老板Prigozhin便是普里戈任,而不是普里戈“津”。
那么,读者就要问了,“zhin”跟“津”的音很近,跟“任”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,为何正式译名反而用“任”?
我猜想,这应该是从最早的译名流传下来的,日子久了,就成为了权威。
好了,既然如此,最早的译名为何音译成“任”呢?
我猜想,很可能最早音译这些外文的都是中国南方人,比如江浙人、客家人或潮汕人。

在上海方言当中,“任”念作[gnin]或[zen];在无锡话念作[zhen213];在苏州话念作任[zen231] ;在客家话念作[ngim4];在潮州话念作[rim6];这些都跟俄语“zhin”颇为接近;如果最早音译“zhin”这个俄语音节的是中国南方人,把它音译为“任”就相当顺理成章了。

另一个例子是Obama,按普通话标准,音译为“欧巴马”更为贴近,但是,当年很可能译者是南方人,所以音译为“奥巴马”。“奥”在闽南语、粤语、潮州话的发言都是“O”。
言归正传,由于“普里戈任”被写进了俄语姓名译名手册,因此,就以它为规范。

同样的原则,Trump音译为“川普”比“特朗普”感觉更为接近,但是,由于《英语姓名译名手册》以及后来新华社译名室委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《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》都用了“特朗普”,因此,就以它为规范。
人名和地名当中,以南方方言为音译基础的这类例子还很多。最好的两个例子就是“瑞士”“瑞典”。
在普通话中,“Swiss”“Sweden”的第一个音节不可能音译为“瑞”,可以音译为“sui”或“shui”,例如“绥士”“隋典”。

但是,在南方方言里,“瑞”的发音就是“sui”,例如闽南语、潮州话、客家话,都是“sui”。因此,Swiss音译为“瑞士”就很可以理解了。
二十年前,我的马来西亚籍华人老板,他提到瑞士时,总是说“睡士”。因为他祖籍闽南。
新加坡也有很多例子,初来乍到的中国北方人经常感觉莫名其妙。

例如:Bukit Timah音译为“武吉知马”而不是“布结提麻”,这是因为在闽南语当中,这四个音节的相应的汉字就是“武”“吉”“知”“马”;当年音译这个地名的时候,新加坡通行的是闽南语,不是官话/普通话,因此,音译地名或人名就很自然地使用最为流行的语言。。
再例如:Jurong音译为“裕廊”而不是“朱龙”。
又例如:Jalan音译为“惹兰”而不是“加兰”。

人名也是同个道理。例如1859年至1867年的新加坡总督Cavenagh,译名是“加文纳”,而非“卡文纳”。
1899年至1901年的代总督Swettenham,译名是“瑞天咸”,这个就是粤语音译了;如果用官话音译,应该是“隋天翰”之类的。

还有一种地名的翻译很有趣的,就是先用闽南语音译,之后改为普通话音译,例如Tuah Road,在1952年的时候,音译为“带路”,因为闽南语“带”就是“Tuah”;后来,到了1970年,就改为“杜娃路”。
交易商排行
更多- 监管中EXNESS10-15年 | 英国监管 | 塞浦路斯监管 | 南非监管92.42
- 监管中FXTM 富拓10-15年 |塞浦路斯监管 | 英国监管 | 毛里求斯监管88.26
- 监管中axi15-20年 | 澳大利亚监管 | 英国监管 | 新西兰监管82.80
- 监管中GoldenGroup高地集团澳大利亚| 5-10年85.87
- 监管中Moneta Markets亿汇澳大利亚| 2-5年| 零售外汇牌照80.52
- 监管中GTCFX10-15年 | 阿联酋监管 | 毛里求斯监管 | 瓦努阿图监管69.35
- 监管中IC Markets10-15年 | 澳大利亚监管 | 塞浦路斯监管91.81
- 监管中金点国际集团 GD International Group澳大利亚| 1-2年86.64
- 监管中VSTAR塞浦路斯监管| 直通牌照(STP)80.00
- 监管中CPT Markets Limited5-10年 | 英国监管 | 伯利兹监管91.56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