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融时报专栏作者贾南·加内什的文章说,回顾过去,美国2024年的大选实际上在2020年8月12日就已定局。那天,拜登选择了哈里斯作为竞选搭档。鉴于他的年纪,这一选择使她在中期内具备了领导民主党的优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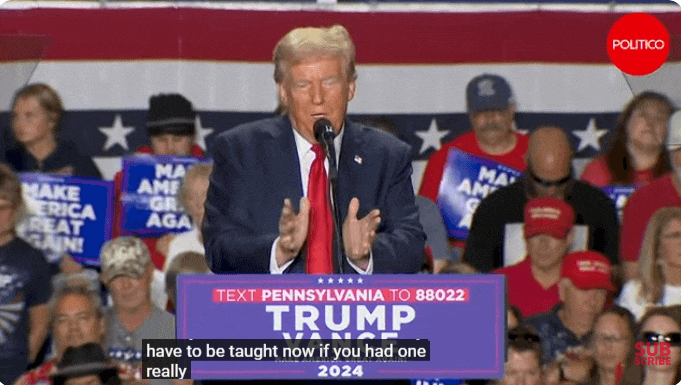
当时在自由派圈子里对这一选择表示怀疑,是孤独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四年后,也许这种观点更易被接受。
在对阵特朗普的竞选中,哈里斯表现并不差。她没有出现决定性的失误,通过了两个主要考验:民主党大会演讲和一对一辩论。
但她的想法模糊不清,言辞有时让人困惑。
此外,她还与一个极度不受欢迎的白宫紧密联系在一起。高通胀对现任者几乎是难以承受的打击,问问英国前首相里希·苏纳克就知道了。
这尤其适用于那些在早有警告的情况下,仍然大肆撒钱从而推高物价的执政者。民主党需要一位不那么与拜登和拜登经济学挂钩的候选人。
如果这只是一个用人失误,民主党或许会悔恨并继续前进。
但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党错误。最近假装拜登能够连任,直到电视辩论揭穿了这一幻想。民主党也没有选择宾夕法尼亚州长乔希·夏皮罗作为竞选搭档,他在关键州的支持率很高。
总有看似“不可避免”的理由促成这些选择,但实际上,这些“理由”是糟糕的判断,甚至近乎失职。
民主党对权力不够认真,其他人则必须承担后果。
这些后果是什么?新任总统可能会在任期内做些什么?
有理由相信,特朗普的再任期可能会是“无拘无束”。首先,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。假设美国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仍然有效,他无法在2028年再次参选。
在他的第一任期,连任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行为。
现在,他几乎没有理由去考虑未来,或许除了有意让自己的子女进入政坛外。
此外,特朗普的首个政府中,有许多像雷克斯·蒂勒森和加里·科恩这样的人,他们放在小布什政府中也毫不违和。而现在,他更可能组建一支与自己风格相似的团队。
与2016年不同,现今已有了一批“特朗普派”的干部和党羽。如果他想削减对乌克兰的支持,或削弱北约,或干涉法律程序,谁会在内部对抗他?
当总统频繁进入“执行时间”时,副总统的影响力会加大。过去是迈克·彭斯,一位右翼但传统的政客;而现在是万斯。再加上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,未来至少两年可能会充满动荡。
当然,一部分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令人害怕。特朗普的敌意是有选择性的,集中在非法移民、媒体批评者以及挑战他的法院上。
尽管这些可能令人不安,但多数选民觉得自己不会受到影响。与佛朗哥或墨索里尼那种全社会的压迫完全不同。
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是理解特朗普的正确视角,但许多评论者仍用其来分析特朗普,因为他们对二战及其原因了解甚多。
但今天,其他选民以及许多外界人士可能没有那么轻松。
那么,什么想法可能会让他们稍感安慰呢?首先,特朗普已年届78岁,美国的民粹运动可能认为他是不可替代的。此人拥有独特的才能,能够说出令人震惊的话却不显得“地位低下”。
像万斯、罗恩·德桑蒂斯和维维克·拉马斯瓦米等继任者,身上往往带有一些网络聊天室的特质,无法相比。
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,或许会促使其他民主国家更多地自我防卫。
法国人这次选举发表了最精辟的评论。法国议员本杰明·阿达德说,“我们不能每四年让威斯康星州的选民决定欧洲的安全”。
特朗普指出,二战过去了人类一代人之后,欧洲和大部分自由世界依然依赖美国提供最终保护,这确实有些奇怪。从德国到日本,这一情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,现在有了新的动力。
顺便提一句,英国原本对脱欧后自由贸易的希望可能也将破灭。特朗普更倾向于实施普遍关税,而不仅仅是对中国。
选举结果的最后一个安慰之处在于,这或许能唤醒民主党。
这个党长期以来有些类似贵族宫廷的特质,对资历的尊重往往超过了对能力的重视,同时也乐意回避一些棘手的问题。
这或许是自由派特有的性格特征,比如英国的工党就在埃德·米利班德和杰里米·科尔宾身上浪费了十年。但是,当一个党是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两个主要政党之一时,这些特质就更为重要。
民主党对选举表现不佳者的宽容,影响到了乌克兰、中东等地区。
政治上最重要且可控的变量是候选人。理念当然也很重要,但理念往往来源于个体。
当哈里斯在2020年初选中几乎垫底时,历史在提醒民主党另觅未来领袖。然而,民主党未能做到这一点,这相当于放弃了一场可以获胜的选举,甚至可能不止如此。
美国革命250周年纪念将由特朗普总统主持。对一个精心设计的共和国,最好的致敬大概就是一次压力测试,如果能通过的话?









